程不时博客链接:http://chengbushi.blog.ch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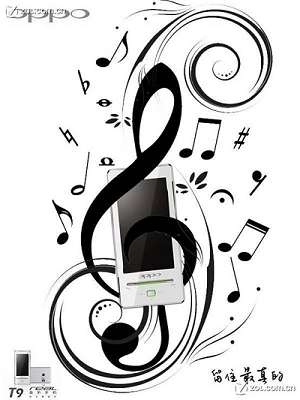
几天前,我国航天战线的开辟者钱学森老人离开了我们。钱老也是我国工程界的泰斗级人物,倡导过许多新的科学思想(如系统工程)和宏观思维,唤起我们对发展全局中某些方面的注意。近几天,媒体纷纷披露钱老最后阶段系统思考的一个课题,是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联系到钱老曾多次谈到科学教育应与艺术教育结合来促进创造性人才成长的主张,我找出多年前我为《中国科技报》写作的一篇谈音乐对科技思维的启迪的文章,今贴到网上,作为对钱老呼吁的一种响应,也是对钱老不断勤勉思维的缅怀,供网友们参考。
音乐与科技工作者的素养
国内外不少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卓有成效的理工科大学,却有着音乐教育的传统。无独有偶,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科技界人士,又同时是音乐爱好者。(这里只举爱因斯坦和钱学森两个例子吧。)音乐对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成为一个绕有趣味的问题。
我在大学时代,曾选修过音乐课程,担任过大学的小提琴独奏手和管弦乐队的指挥。至今我从事飞机设计已三十余年,仍然保留了欣赏音乐、演奏小提琴、及作曲和为合唱合奏编写合奏谱的爱好。有人问我:音乐对于你的飞机设计工作,在哪一个具体技术问题上有过启发帮助?我无法回答。
当我把我的窘态告诉东北一个飞机工厂的总工程师时(他也是一位音乐受好者),他说,他清楚地记得上中学时数学老师上第一堂课时讲的第一句话,至今记忆深刻得益不浅。那老师说,你们学数学主要不是学会具体的解题公式,而在于对思维的训练。数学尚且如此,音乐的作用岂在于解决一两个具体问题?
音乐,并不是鸟鸣风吼的简单模拟,人们在充满喧闹的城市或海边,听到的也不是可以称为音乐的声响。音乐对客观世界的摸拟并不限于在音响上,单纯在音响上模拟现实的音乐反而被认为是下乘之作。现代科学研究指出,音乐对现实的模拟在另一个特定的方面,就是音乐(特别古典音乐)具有1/f节律。这是一种既有连贯演变、又间有意外变化的过程。人世间许多宏观现象都有这种性质。比如人生的经历、历史的演变、地平线上山势的变化、甚至人的思绪的展开,都具有这种既非完全杂乱无章,又并不是有了开头必知结尾的特性。音乐本是思维的产物,在这个特定的方面反映了思维的活动特性,从而在欣赏时使人引起共鸣的愉快。
当然,音乐主要是一门艺术,对人的趣味和情操进行陶冶。我在这里只举无词的器乐作品,因为用人声演唱的歌给人的感觉中,还多了歌词的文学性因素。而器乐则单纯是声音给出的感受。比如在古典音乐的极多的小品类别中,人们可以从各种“夜曲”中欣赏到恬美、从“摇篮曲”中感受到深情的抚慰、从“牧歌”“船歌”中领略到开阔和摇荡、“传奇曲”叙说着古朴久远的故事,从“思乡曲”中聆听到对故乡凄惋的眷恋、从“进行曲”中感受到雄伟壮丽、从各种“舞曲”中领受到民间的欢愉和奔放等等。此外还有各种奏鸣曲和交响曲,以几个乐章的庞大结构,用忽而庄严深刻忽而柔美抒情,忽而轻快跳跃,忽而激情澎湃的音乐形象,以很大的情感幅度来表述了从黎明到月夜的景色、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幻、展现从沙漠到海洋的不同风光、描绘出人生的兴衰起伏、抒发着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情调变化,演绎着从豪气四溢到哀怨悲怆的各种人生体验。我们从长期来人类用智慧和情感积累起来的音乐文化宝库汲取养料,无疑可以大为丰富对世界的感受能力,使我们的情操得到陶冶。
宇宙是完整统一的。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的各个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些联系。音乐对思维的启迪,是很值得重视的。
音乐是“发散思维”的范例。独创性是所有创作的共同要求。但在音乐中得到突出的强调。如果说在绘画中有时还可以模仿别人的风格作画,那么在音乐中如果一个作曲者的格调与某一大师相同,则最多只能成为游戏作品。
由于这种对独创性的强调,音乐中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多样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德彪西的钢琴曲《月光》、以及德沃夏克在《水仙女》歌剧中的《月光》咏叹调,同样以月光为名,但是就音响的组成来说却极不相同。每一部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又都不相同。至于“变奏曲”中围绕主题创作出那样各有情趣的变奏来,对于发展思维的灵活性也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我还感到音乐是一种结构、是一个系统、在这些方面,与我们日常工作的工程世界也有相似性。
音乐由不同的音高、音色、音强、和声和节奏的一连串音响在时间坐标构成一种结构,从普通民歌的单段体、两段体、三段体发展成为包括几个乐章,每个乐章又有几个乐段、包括好几个主题的庞大曲式结构。宏伟的作品不但使人感到作曲者澎湃的乐思和激越的感情,还可以使人欣赏到作曲者从简单的“音乐动机”发展成为乐句、乐章和整部作品的精美的匠心。无论音乐的创作、演奏或欣赏,都需要一种在宏观上掌握这种结构的能力。
一个钢琴手如果手脚不协调,或者两只手不协调,甚至两个手指乱了套都会毁了音乐。更不要说一个不称职的指挥,或者由不称职的演奏员组成的乐队奏出的会是什么音乐。我在飞机设计工作中常希望我的工作集体、以及飞机上每个技术组成部分能达到交响乐般的协调。而一部交响乐,真是一个很理想的和谐范本。
从单纯肌体动作方面,我还觉得演奏乐器是一种很好的“左手操”。近代脑科学认为人的左右半脑有分工:左脑主要司语言逻辑、数学和演绎,而右脑司形象和想象。一般人左脑负担过重而右脑锻炼不足,使整个智力受到抑制。而演奏乐器时,大部分都需要发挥左右手能力。我觉得通过演奏乐器来激发右脑功能,比专为锻炼右脑而编出枯燥的“左手操”愉快得多。
此外,我还认为练习作曲是极好的创造性练习。作曲需要遵循很多规律,这是人们从长远的音乐文化中总结出来的。但是在这些规律范围之内又可以容许无限的变化。必须有想象才能创新。这难道不正是任何领域内的创造活动(包括工程设计)中所遇到的情形吗?
飞机设计师的创造活动受到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并不能每天都设计新飞机。但休息时创作新曲的活动却可以任意进行。正如运动员在训练场上蹦跳是为下一次比赛做准备一样,飞机设计师在业余时间练习作曲,说不定在为下一个飞翔蓝天的雄鹰在锻炼自己呢——只不过不是锻炼排球扣杀的臂力,而在于思维飞腾的创造力罢了。
(按:此文曾载《中国科技报》1986年11月4日4版头条)
程不时 博客文章
2009-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