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博客链接:http://blog.sina.com.cn/jiangxiao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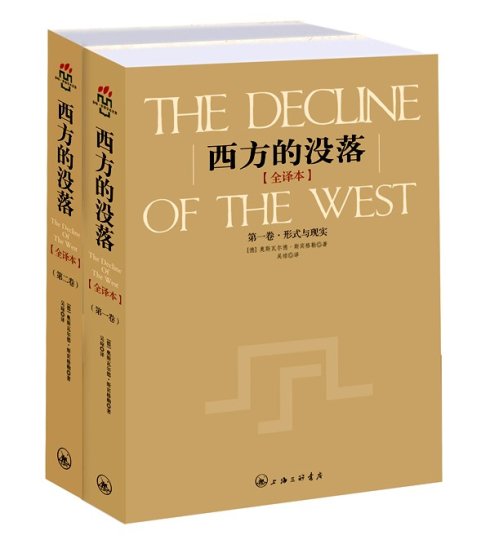
《西方的没落》(两卷全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著,吴琼译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定价:99.80元(全二册)。
整整100年前,寂寞的辞职中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慕尼黑一间小破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撰写他的传世巨著《西方的没落》。窗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他生活拮据,衣食不周,冬天供暖也没有保障。多亏了他身体一直不好,两次应征入伍都被退回,否则他有很大的概率像一条狗那样死在前线肮脏泥泞的战壕里。
施本格勒出身平民,但受过较好的教育,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读书,24岁在哈雷大学拿了博士学位。30岁那年他继承了一笔算不上丰厚的遗产,可以让他维持生计,于是他第二年便辞职隐居,开始撰写《西方的没落》。一个在学术界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忽然写起这样的大书,当然会让人感觉很不靠谱,第一卷“形式与现实”几经周折,才于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初版仅印1500册。
但是《西方的没落》总是让我联想到中国两千年前一首著名歌谣——李延年《佳人歌》中的句子:“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西方的没落》第一卷问世之后很快引起轰动。一个年轻作者,居然睥睨一世,议论纵横,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顿时迷住了各界读者。一时上至政要,下及平民,都在谈论《西方的没落》。学术界的衮衮诸公则照例出来指摘书中有许多硬伤之类。那时施本格勒血气方刚,他再接再厉,于1922年推出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并推出了第一卷的修订版。两卷出齐,正合一顾再顾之旨,一部经典作品从此流传世间。
《西方的没落》堪称煌煌巨著,中译本两卷达150万字。这当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施本格勒继承了前辈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布克哈特(J. Burckhardt)《世界历史沉思录》之类著作的浩大文风,神游万里,思接千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论述起来根本不拘泥于编年和史事。如果一定要将它归类于历史著作,那也只能是“史论”而非“史学”。而施本格勒自己对此书的定位则是:“我还是可以自认并骄傲地称其是一种德国哲学”——是哲学而非历史。也可以说,历史只是他哲学沉思的对象,或者说是文化研究的对象。
《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铿锵有力,夺人眼球,极具耸人听闻的效果。其实施本格勒并不是要扮演预言家,预告西方的没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要“预断历史”。但是“没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用大白话来说,施本格勒只是指出,世间所有的文化或文明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生老病死,西方文化也不例外,所以他只是断言“西方终将没落”。
施本格勒不用所谓“史学家的严谨”来表达他的思想,事实上他的那些思想也只适合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达。在行文中,他几乎不作任何“论证”,只是干脆利落地给出一个又一个的“论断”。这使他的书读起来渊博浩瀚,酣畅淋漓。例如他认为在“文化”阶段是创造的,继之以“文明”阶段则是反省和物质享受的,所以结局只能是没落。施本格勒认为,西方的这种没落过程会持续几个世纪。
施本格勒在书中表白说,是歌德给了他“方法”,而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不过对于这种话,通常都不能太当真。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所谓“观相学”,这又被他称为“世界历史形态学”,大体上有点类似中国古人的“见微知著”。事实上,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就有许多古人见微知著,即根据某些具体现象而对国政乃至国运作出判断的事例。
施本格勒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他将这样的历史观称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而他“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这种较为平等、多元的历史观被他喻为“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
他还试图为各种文化寻找玄之又玄的“原始象征”,例如:古典文化的原始象征是“就近的、严格限定的、自足的实体”,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征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阿拉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世界洞穴”,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没有边界的平面”,而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则是“道”。
他对阿拉伯文化似乎情有独钟,在第二卷的14章中居然独占了3章的标题。对于中国文化他谈得很少,却注意到“在周朝初期,有对于冥界诸神和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有各种神秘宴饮的仪式,在那里祭神与狂喜的集体舞蹈如影相随;有神灵与女祭司之间模拟性的表演和对白”。作为一个终生未娶的男人,他在书中也说了一些诸如“男人创造历史,女人就是历史”、“女人的策略永远都是征服男人”之类的老生常谈。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最后一章是“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B)机器”,这一章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虎头蛇尾草草了事的一章,其实未必。施本格勒似乎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半个世纪后尼尔·波兹曼(N. Postman)所哀叹的局面必将出现——文化向(由机器所表征的)技术投降。全书以古罗马经典作家塞涅卡(L. A. Seneca)的名言作为结尾:“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Ducunt Fata volentem, nolentem trahunt),充分表达了施本格勒对西方文明这种宿命的无可奈何之感。
百年之后重读《西方的没落》,着实让人别有会心。西方看来真的是在没落了,而且没落的时间很可能比施本格勒预断的更早——施本格勒明确说过:西方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考虑到这是100年前的预言,还真有点先哲风范。
唯一的问题是,在施本格勒写书时看上去早已“没落”成为定局的中华文明,居然奇迹般重新振兴,而且隐然已有再度如日中天之势。在施本格勒看来,所有文明都有生老病死,概莫能外,但中华文明已经持续了五千年,这一点毕竟是所有其他文明都未曾做到的,面对这一文化特例,或文明异数,施本格勒若泉下有知,会不会重新建构他的理论框架?
(载2015年4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
江晓原 博客文章
2015-04-14






